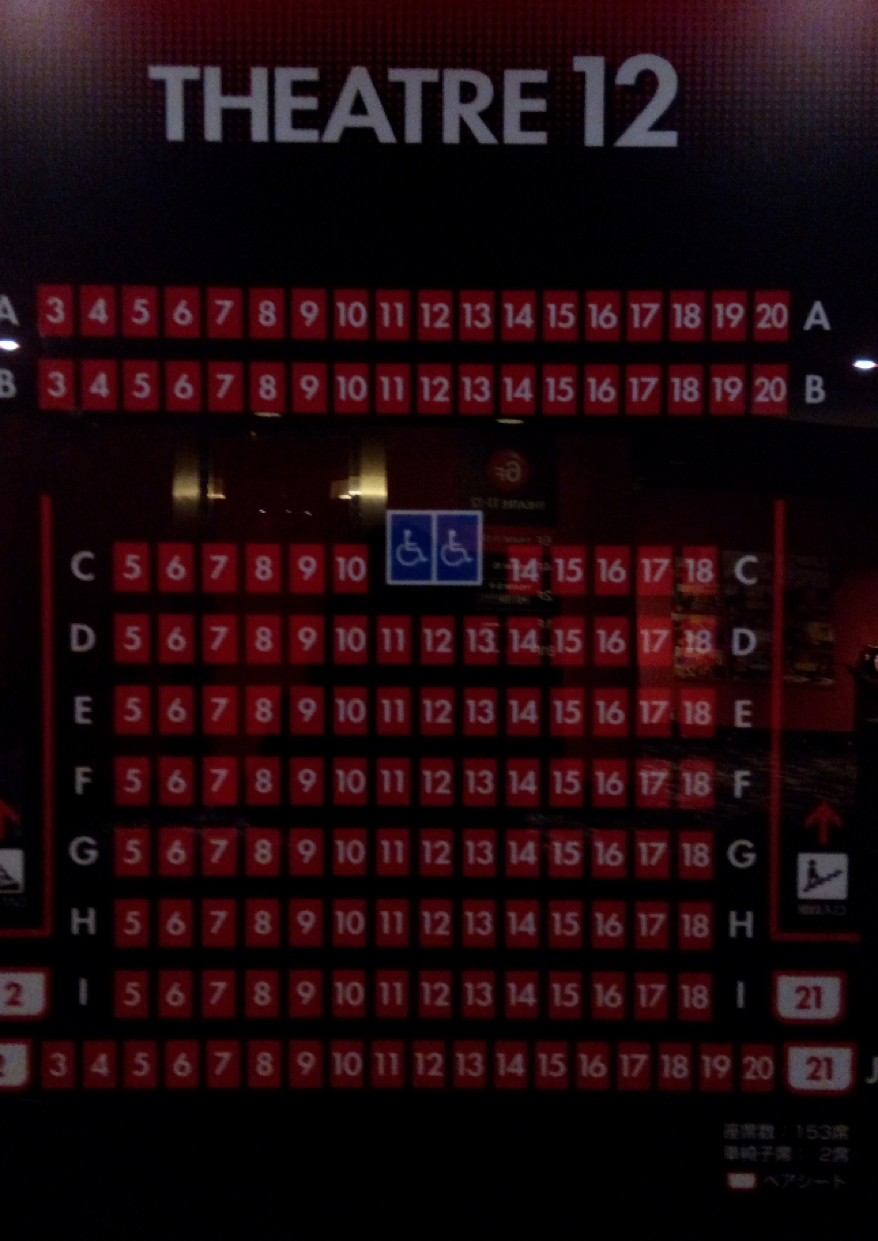作者:孫嘉梁 博士(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常務理事)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免費授權,畫家:高更
我初次觀賞這部電影時,整個覺得很荒謬:我覺得,鹿野先生是一個完全活在自己世界,完全都不在乎其他人感受的人。但是,為何這種人身邊還有一大群人自願地支持他如此任性地過生活呢?為什麼他敢在一群正在協助他洗澡的女生面前,說出色色的話呢?為什麼他敢利用其他人對他這個重度障礙者的同情與牽掛,來實現自己的心願,並且怡然自得,而不會感到愧疚呢?
我第二次觀賞這部片時,雖然不再覺得這個故事如此荒謬,對於鹿野先生的負面觀感也少了許多。但是,剛才提出的這些問題仍然在我心中迴盪。
換個角度想,人與人的關係是互相的。或許,我該好奇的是:為什麼存在著一群足以支持鹿野先生「做自己」的志工?即使他們知道鹿野的父母都還健在,即使他們必須冒著一定程度的法律風險來進行具有某種程度危險性的協助工作,例如抽痰。我甚至在思考,如果將這些志工換成「有給職」的「個人助理」,那麼「角色的改變」對於這個「協助關係」會有什麼影響?
我相信,這部電影不只是一個關於重度障礙者生命奮鬥歷程的故事。它更想描繪某種「資本主義社會」裡「難以想像的社群關係」。
「鹿野家族」(編者按:以鹿野這個人為中心形成的另類家庭;並不是指原生家庭)帶來的驕傲認同感,能夠單純用錢買到嗎?
我並不意味著「協助障礙者的工作」都應該「做功德」。實際上我非常反對這種「功德說」;因為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很容易將「被協助者」是為需要被救濟的「客體」。抱持這樣「功德說」想法的協助者,最終應該都會變成電影中,認為鹿野先生「很享受人生」,不是需要被救濟的對象,而用電話辭職的那位志工吧!
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障礙者的個人助理會得到「物質報酬之外的成就感」?想想電影中,志工美咲看到接受氣切後的鹿野,在暗地裡不斷嘗試後,終於拿回自己唯一的生存武器--說話的能力。 美咲在旁,感覺到瞬間難以言說的感動!
支持一個人能夠在生活中做自己,與在高科技商品生產過程中擔任一顆螺絲釘,何者比較有價值?答案應該因人而異吧!
如果國家投入足夠的資源,讓重度障礙者不但可以不依靠原生家庭而生存,還能夠活出自己的個性,追求自己的夢想,打破社會上對於我們的刻板印象,或許我們的「個人助理們」就更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價值與意義。事實上,如果真正依據我國法律上要求「讓障礙者與其他人平等地參與社會」這項原則來投入資源,就能夠讓「支持障礙者生活」成為一個足以維生的職業。
電影中也毫不避諱地呈現鹿野先生的情慾需求。令我有些困惑的一幕是:為何鹿野要求志工田中與他一起觀看成人影片?這一幕或許在問,整個社會應該迴避重度障礙者的情慾,以避免尷尬?或者這樣的刻意迴避反而更尷尬?如果把自己的情慾轉化成追求心儀對象的動力,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那麼自己解決生理需求,不也是一個,同樣正常的選擇?
田中能躲到角落自慰,鹿野能夠有這種選擇嗎?當自己心儀的志工美咲無意間發現書架上的情色雜誌時,鹿野推托地說:是其他志工留下來的!美咲卻率直的提出自己對於「重度障礙者是否有性慾」的疑問。如果鹿野那個帶著醫學常識的回答,讓美咲覺得自己的問題很蠢,那麼社會上大多數人對於「重度障礙者性慾」的認知是否同樣地蠢?或著是以「視而不見」的敷衍心態來面對這項人的基本需求?
劇情中另一個有趣的部分,是田中替鹿野寫情書給田中自己的女朋友美咲,並希望美咲答應鹿野的出遊邀約。田中並沒有察覺,自己是利用女朋友來實現對於鹿野的憐憫;但被利用的美咲在第一時間就感受到自己「被男朋友(田中)推給另外一個男人(鹿野)」。
田中的不察,或許是已經習慣現實中「講究條件」的交友潛規則,根本不認為喜歡美咲的鹿野,對自己會造成任何威脅。另一方面,當他知道,美咲當初為了參加與醫學系學生聯誼而謊稱自己是大學生的時候,卻一時無法分辨「自己喜歡的到底是美咲、還是她所謊稱的身分?」;而將自己的焦慮轉化成「對父母說謊」的擔憂,將這個對於情侶關係的考驗簡化成「誰先說謊」的問題。美咲為了認識「理想的對象」而假冒身分,而田中為了留在「自我感覺良好」的舒適圈,以「責怪美咲說謊」的方式,來逃避無法釐清自己心意的事實。或許每個人為了達成目的,某種程度上都需要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對於美咲而言,比起男朋友田中,鹿野先生似乎更能滿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我們無法知道美咲是否曾經愛上鹿野, 但當田中諷刺美咲做善事竟然可以做到「差點跟鹿野先生上床」時,美咲反唇相譏地回應「你怎麼知道不是真的愛?」,讓田中明白這真的是一段潛在的三角戀,也想把田中因為自卑而築起的優越感圍籬打碎!
無法否認地,鹿野先生還是一個「高度活在自己世界裡」的人;這樣的個性可能是由「身體功能」、「人生目標」與「社會制度」三者共同形塑而成。身為一個無時無刻需要他人協助的障礙者,身處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公共支持制度的社會裡,他仍執意實踐自己設下的人生目標:確保自己能夠享有與其他人同等的自主性,並且不讓母親因為愧疚而將餘生全部葬送在照顧工作上,更要讓社會知道:即便需要全天候的人力支持,一個重度障礙者仍然可以既不住在機構也不依賴父母而生活。對於大多數非障礙者而言,這些都是對人生的合理期待;然而鹿野先生在實踐這樣些目標到過程中,卻必須不斷地接受挑戰:即使在無數次爭吵、替換與磨合之後,仍然必須經歷志工臨時請假、必須及時找到代班人員的慌亂與不安全感、也必須承受陪伴過夜的志工因為疲累而產生的情緒。
這部電影縱然包含了一些「勵志」的元素,但我認為「真實」才是貫穿全片的主軸。在鹿野先生克服重重困難之後、離開醫院而重返「自立生活」的慶祝餐會上,他突如其來地向美咲求婚的那一幕,令我印象深刻。「想跟美咲永遠在一起」是鹿野真實的心意;但是,一個「勵志的生命鬥士」並非總能得償所願,這才是真實的人生。品嚐著求婚被拒絕的苦澀,鹿野先生卻有機會了解自己在美咲心中是「一個偉大而重要的存在」。鹿野先生看似任性,卻仍在意自己的「重要他人」的幸福:他選擇從輪椅上摔下, 冒著生命的風險,就是為了看到田中與美咲和好。
無論這部電影與其原著小說的內容,帶有幾分真實、幾分杜撰,這部文學作品都讓大家看到重度障礙者真實的生命處境,以及,當我們能夠跳脫功利主義的思想箝制時,這樣的生命可能與社群發生怎樣的關係?或許,當人們看到了這些,就不會輕易地認為支持障礙者自立生活的各種制度,只是為了「保障人權」的資源耗損;反而能夠開始思考,「人權」的觀念帶給人類文明什麼樣的啟示?
在這個生產力達到人類史上前所未有高峰的時代裡,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既能保障每個人的自主性,又能防止人際疏離而產生的孤寂與不安全感?如果一個社會制度能夠支持重度障礙者有尊嚴的自主生活,讓每個人都享有尊嚴並感到安全的社會制度,那就好了。這種境界,真的是台灣整體財政無法負擔的嗎?或者,台灣財力可以負擔,但資源分配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