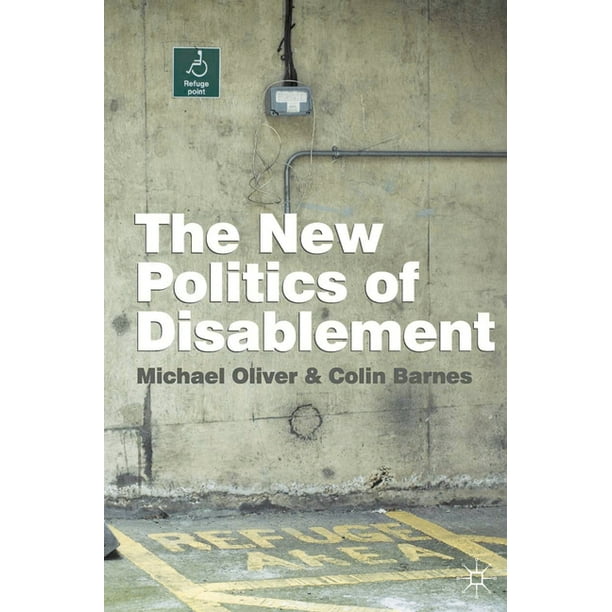作者:江家欣 (社會工作師 /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博士生)
本文是由關懷障礙權益之明眼障礙研究者,閱讀藍介洲所撰寫的《視障者的機智生活》後進行讀後整理,再結合自身所蒐集之資料而成的台灣視障者生活現況反思。
作者致謝:
「特別感謝視聽障朋友靖騰、視障朋友玉緯及禹豪,提供寶貴的經驗與知識,讓這篇文章在障礙者的視角下更加完善。」2024-10-18 updated
壹、 一本視障者所寫的書
選擇這本書做為反思的參考,是因為台灣以障礙者為主體的書籍原本就少,更遑論由障礙者所撰寫之書。藍介洲不僅僅是全國首位全盲社工師、台灣大學社工所博士、也是現任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秘書長,更是一位後天全盲者。他以障礙者本人的立場進行書寫,讓障礙者的經驗不再「假他人之手」被迫二手轉譯,更能向大眾直白展示視障者感知的世界。
說到這裡,應該很多人會好奇,視障者究竟如何閱讀?又如何進行書寫呢?以下我們將分別由視障者的閱讀、書寫、外出、娛樂及其與社會標籤的互動進行討論。
貳、 視障者也可以「讀」書
以衛福部於2024第2季所公布之官方資料可知,我國目前身心障礙者總人數約1,223,392人,其中194,240為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者,換言之,我國障礙族群中約有15.88%的人口為廣泛的感官障礙者,其中,視障者又可以分為具有剩餘視覺,可以看見粗大影像或者模糊輪廓的低視能者,及大眾較為熟悉的全盲視障者。
以低視能者來說,依據不同的障礙程度,可以藉由平板、擴視機、放大鏡等輔具進行閱讀。然而,全盲者該如何閱讀呢?作者藍介洲告訴我們,除了最傳統的視障輔助人力外,全盲視障者也有自己的閱讀法寶,在此區分為智慧型手機、盲用電腦,以及點字和有聲書。
電腦(智慧型手機):
拜科技進步所賜,目前的手機只要開啟「視覺輔助功能」,當事者輕觸手機螢幕,手機就會跟著指尖滑動的位置一一報讀。如同作者藍介洲所述:
「智慧型手機就像盲用電腦一樣,讓我們視障者在資訊社會裡也可以「看到」各種文字或網路訊息。但美中不足的是,目前對於照片的辨識能力還極為有限,我們還是沒辦法知道「網美照」裡的人物與景色,到底有多美。(p.43)」
不過,針對無法知道景物多美這一點,在科技突飛猛進的今日,拜AI所賜,如今只要搭配適當的指令,就可以由AI產出人性化「口述影像」,相關工具包含蘋果系統的『旁白』、安卓系統的『TalkBack』、Be My Eyes 的 Be My Eyes – Helping blind see、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 Microsoft Copilot,及最常見的 ChatGPT。。
舉例來說:當我向ChatGPT表示「我是一位視覺障礙者,可以請你幫我口述影像嗎?」,並且貼上下圖(照片為本文作者江家欣所攝)時——

我得到的回應如下圖:

再舉例,當視障者出門在外,需要有即時的口述影像時,使用Be My Eyes的Be My Eyes – Helping blind see拍下欲轉譯之畫面,就可以得到以下口述資訊。(照片為本文作者江家欣在咖啡廳拍打貓咪屁股時拍攝)

所以,在科技與社會的交織下,視障者的經驗與想像便能在科技的擴充下,突破環境的重重限制。
盲用電腦:
盲用電腦基本上就是一台加裝了輔助軟體的筆記型電腦,不論外觀或重量都與非障礙者使用的電腦毫無二致,他的主要功能在於將電腦螢幕上面的文字唸出來,並且可以依據視障者的喜好調整語調、語速及語言。所以,不論你今天想聽的是女人、男人、老人或者小孩的聲音,盲用電腦都可以做性別與年齡的自由時刻轉換。不過,盲用電腦畢竟只是機器,只表音不表意,就可能造成如「“我解脫了”和“我姊脫了”」傻傻分不清楚的尷尬情境。
另外,盲用電腦也可以搭配點字觸摸顯示器使用,讓視障者除了聽書之外,得以用觸覺的方式,將盲用電腦上面的文字轉換成點字,「摸」出訊息。
然而,在此我想提出兩個值得反思的點,第一、盲用電腦只有國際化,卻沒有本土化 ; 第二,科技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從屬關係。
針對第一點,因為目前盲用電腦軟體多為國外所設計,所以視障者在使用盲用電腦時確實至少有80幾種語言可以選擇,包含葡萄牙文、越南、印尼文……等,但,這80多種語言卻不包含閩南或者客家語,只能期待國內展開與工程相關人員的跨域合作,為本土障礙族群的福祉作出突破。
第二,在科技尚不發達、資源過少的年代,視障者想要閱讀就只能仰賴他人的協助,倘若朗讀者語速過快、咬字不清或者視障者因反覆思考而必須重複閱聽,就必須看閱讀者的臉色獲得資訊。然而,當盲用電腦出現,無論視障者想要聽幾次朗誦,盲用電腦都可以不厭其煩的一字一句為你朗讀,不再需要看人臉色求人辦事。這就是科技的好處,改變人與人之間從屬關係的同時,更讓障礙者與身邊他者不再有上下關係的壓力,閱讀得更自在。
點字及有聲書
點字(原名 Braille,為 Lois Braille 於 1830 年發明),中國稱為盲文,但台灣多以點字稱呼,其由六個小點組成。點字和手語一樣,可能因地域而有所不同。舉例來說,雖然中國和台灣都使用中文,聽覺上相同,但點字的使用卻不同,因此台灣的視障者在香港或中國,可能仍會因點字系統的差異而遇到障礙。另,有聲書就如字面所示,是有聲音的書籍,這裡不再贅述。
最後,除了上述三種法寶外,台灣目前郵政系統的「瞽者文件」更在可近性上大幅降低了視障者借閱國內圖書的阻礙。所謂瞽者文件,就是政府各公私立單位要寄送給視障者的有聲書或者錄音資料,都可以享有免郵資的服務,而視障者把資料閱覽完畢後,只要將資料原原本本地裝回原信封,就可以將文件免郵資寄回郵寄單位。所以「視障者想借什麼點字書或有聲書,只要打電話給視障圖書館,他們就會用印有「瞽者文件」的包裹寄給我們。當我們讀完這些書,我們一樣將這些書放入原本來的包裹,再寄回圖書館就可以了!(p.61)」
綜上所述,視障者在語音輔助軟體、盲用電腦、點字觸摸顯示器輔助下,不論是上網查詢文件、臉書發文,甚至成為書籍的作者,都是可以做到的。
參、視障者外出
凡人都有外出的自由與權利,然而在台灣行人的路權卻是出了名的糟糕,對視障者來說更是有如「行人地獄」。因此,在現有制度尚不完備的情況下,視障者都如何外出呢?
最常見的方式之一是聽聲過路,而聽聲又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找到電線桿上面的有聲號誌按鈕,按下之後聽取聲音辨認通行時機。台灣目前以「布穀聲」及「鳥鳴聲」分別代表南北及東西向可通行,「蟋蟀聲」則為行人專用,然而,台灣的有聲號誌不僅稀少、故障率高、設置位置不便於視障者使用、車輛噪音過大難以聽聲、更會因為夜晚車流減少背景噪音降低,而於夜間遭到民眾投訴聲響擾民。第二種,便是找不著有聲號誌,又沒人幫忙,只能用力聆聽車流無奈前行了。
再來就是友善的人導法。我國衛福部社家署CRPD人導法的宣導短片便已經表明,官方帶路法為「問、拍、引、報」。簡單來說,如果我們在外遇到獨行的視障者你想要協助他,第一步就是「問」,詢問視障者是否需要協助; 如果視障者表示願意接受協助,那就進入第二步「拍」,輕拍視障者手背,讓他知道你的相對位置; 第三步「引」,就是以至少半步至一步的距離引導視障者行進; 最後一步是「報」,以口述的方式告知視障者高低差、坑洞及障礙物。當然,除了上述官方操作方法外,也有許多民間的自創法,像是用聲音控制障礙者行徑方向的「聲控法」、站立於視障者後方推著視障者前行的「人肉盾牌法」,更有以白手杖作為橋梁的「老農牽牛法」。
然而,雖然各個方法都是出於善意協助,卻往往忽略對於視障者是否真正友善。舉例來說,「老農牽牛法」雖然可以避免肢體接觸的尷尬,又可以讓視障者跟著引導者調整行徑,維持安全,但是白手杖基本上就是視障者的「類雙眼」,當引路人將白手杖作為與視障者之間的橋梁,不異於剝奪了視障者看見世界的重要工具,反而會使得視障者更加缺乏安全感。
最後,除了上述聽聲過路及人導法,還有最可愛的導盲犬可以協助引路,然而導盲犬的訓練、配合以及注意事項又是另一個大學問,就不在此贅述。
肆、視障者的娛樂
以靜態遊戲來說,視障者也可以下棋、打麻將、玩撲克牌,只不過是參與娛樂的工具有所不同。
以撲克牌來說,視障撲克牌的每張卡牌都會有點字,每局結束都會亮牌並且唸出來給同玩者聽,這樣不論弱視或者全盲都可以一同參與遊戲 ; 而針對象棋與圍棋之類,視障者的棋具都經過特殊設計,例如棋盤有凹槽、棋子有花紋,這樣視障者在下棋的時候,不僅可以辨明棋子,棋子也不會輕易滑動。此外,與明眼棋局不同的是,視障者下棋必須時時說出自己落棋的位置,這樣對手才能摸棋確認,當然也有些資深的視障棋手,因為經驗老道,便乾脆口述下棋,連棋盤與棋子都免了。
以介於動態與靜態之間的博物館參與來說,視障者可以著重觸覺與聽覺做出「非視覺美學」的多重體驗,例如至動物園及故宮旅遊時,館方可以依據動物或者展品的外表、重量、毛髮、粗細、材質……等製作替代展品; 如國立台灣美術館近年所開展的非視覺探索計畫,讓「社群共賞」(social view)成為可能,同時讓視覺不再成為社會參與的唯一方式。
最後,諸如跳繩、舉重、爬樓梯、吊單槓、騎飛輪、登百岳、泳渡日月潭、玩三鐵、攀岩、或者騎車環島,只要有適當的協助,例如專業陪跑員或者領騎志工的加入,就可以讓運動真正「全民」,而不再因環境而被迫「不可能」。
伍、 視障者與標籤的互動
視障者其實不是非得戴墨鏡,有些人是因為眼球萎縮、損傷或摘除,覺得不美觀才會戴墨鏡,但是,有些人則是為了「避免誤會而戴」,這些常見的誤會可能包含坐博愛座的時候看起來不像障礙者而被側目或辱罵,或者如同藍介洲於《視障者的機智生活》所分享的,外出吃飯時眼神不自覺朝著專注聆聽的地方看去,造成餐廳鄰座客人以為視障者一直在瞪人的情形。
所以,為了避免以上不愉快的生活插曲,有些視障者就乾脆以墨鏡「為自己貼上標籤」,省得麻煩。
「平心而論,戴墨鏡或許會有標籤化的可能,就像白手杖一樣。墨鏡長期下來,已約定俗成,成為我們視障者的重要標誌之一。但有些時候為了避免誤會,我們似乎還是有必要向這個社會主動宣告自己視障的身分,為自己貼上視障的標籤,以求明哲保身。(p.213)」
這是一件令我特別訝異的事情,在障礙研究裡面,我們總是致力於撕下標籤,所以我從沒想過「主動」利用標籤以明哲保身,算是以障礙經驗擴充了我對障礙及其標籤互動的另一種想像。
陸、 結語
《視障者的機智生活》是一本輕鬆且易於閱讀的書,台灣視障者相關的資訊網路上也不難搜尋,但是我在閱覽相關資訊時,仍然會對自己的無知感到驚訝!原來視障者除了白手杖還有這些輔具、原來視障者有這些有趣的娛樂器材、原來視障者可以和標籤有如此不同的互動……這些都是嶄新的發現與學習。
最重要的是,撰寫此文進行整理的過程,讓我重新省思到,障礙者的「不能」往往源自於社會對障礙者扁平化的想像,無能化又嬰孩化的預設立場,以及社會對於自身障礙認知有限的意識缺乏。然而,不論是閱讀、書寫、娛樂、交通、運動,甚至戀愛或育兒,只要資源到位就沒有人「不能」,真正障礙的是這個使人障礙的社會,以及使人障礙又缺乏共融的思維。希望這篇短短的反思,能夠淺白簡易的讓大眾一窺台灣視障者的生活,同時擴充大眾對社會共融可能性的想像。